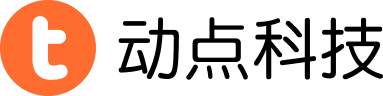当雨大到需要打伞的时候,陈然开始把画笔和颜料一个一个整理好装进包里。她背上包,朝着坐在旁边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说“我先走了”,然后慢慢穿过夜市里正从包里掏伞的游客和挂着白炽灯的摊位。摊位里有把头发染成黄色的贴膜小哥,穿着围裙炸鸡柳的阿姨和看起来像是产自义乌或温州的各式古玩。
一
陈然每周六来吴山广场画画,她跟“鸭舌帽叔叔”说“你让我在这画,我画出来的钱我们五五分”,“鸭舌帽叔叔”说“好的”。
她最初把这当作一种爱好,后来变成一种习惯——就像闲不住的广场舞团和每天接两单的Uber司机一样。很多时候,当人们养成习惯时,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仪式感。对陈然来说,这种仪式从背着画笔等公交车开始,到吃完益乐路的一碗藕粉结束。
“这里的藕粉不行,都是给游客吃的。”陈然说,当时她正经过清河坊的小吃街,要去中河高架桥下乘公交车。有时候离开的早,她就从吴山广场朝北走,走过湖滨商业街上举着旗帜的导游和举着自拍杆的游客,比起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上演的一幕幕人生百态,他们显然更喜欢雨天里像是加了层滤镜的湖水,和藏在雾气背后羞涩的山丘。
陈然在去年底开始去吴山广场画画,她给来往的游客们画像。早先游客们会亲自做模特,碰见漂亮的姑娘,“鸭舌帽叔叔”还会精心准备合适的灯光。不过陈然没赶上好时候,她去的时候“鸭舌帽叔叔”已经放上了一块写着“可画手机自拍”的纸板,陈然对那些模糊的照片和五花八门的滤镜颇有微词——“画的漂亮吧,就说不像,画的像吧,又嫌不好看。”
大概夜里十点半,陈然在古荡下车,她在这里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张铺满画纸的白色桌子和在四月份会散发出一点霉味的木制衣柜。不过在回家之前,陈然要在楼下吃碗藕粉——杭州人把藕粉作为这里的知名特产,尽管它似乎并没有嘉兴粽子和宁波汤圆那么出名。在余杭区的三家村农贸市场,有一个1997年就注册成立的“杭州市余杭区藕粉协会”,这里出产的“三家村藕粉”是杭州藕粉界的翘楚,它们被送往各个特产商店与旅游景点,跟着游客抵达一个个异乡陌土。
二
陈然工作的地方在拱墅区的A8艺术公社,该公社名讳取自“Art”中的“A”与“八丈井28号”的“8”。在2010年,A8艺术公社曾获得了一个“中国文创产业品牌园区”称号”,这里入驻了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文化创意公司,陈然的公司为大大小小的游戏开发商提供美术外包服务,她在里面的工作也是画画。
如果男员工的头发长度能代表其艺术造诣的话,那么这家公司的专业水准势必冠绝八丈井新村——他们时常接到一些知名开发商的订单,比如卡普空、Deep Silver和南梦宫万代。这些来自国外的大客户对美术的要求相当苛刻,在做之前那份工作时,陈然从没想过画一个游戏角色要先看一份上万字的文档。
“里面会告诉你这个游戏里的文化和环境,这个角色的背景、经历和性格,有时候还精确到他爱吃的东西和口头禅,然后你根据这些材料去构思角色的相貌和穿着,穿着也得符合游戏的文化才行。”陈然说。她往往要画十几个形态迥异的人物,尽管开发商要为所有设计出来的角色付费,但他们最终只会选定一两个。
“有一次一家游戏公司要设计游戏里的武器,让我们画了三十个,最后就选了一个。”
“那剩下二十九个不是浪费了。”
“不会的,会有中国的游戏公司来买挑剩下的。”
三
由于美术工作的成本实在太高,大部分游戏开发商会把这部分工序外包出去。尤其是一些小型团队,由于养不起一整个美术团队,他们就从美术开始,把能外包的工作全都外包出去。在两三年前手机游戏的爆发期,这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诞生了无数外包服务提供商。
陈然公司的隔壁是一家音乐外包商,他们的工作是把拍大腿的声音变成游戏里的马蹄声。不过他们同样为游戏制作配音与背景音乐,整支团队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这些演员能够留意到难以察觉的细节问题,避免让游戏的配音变得像70年代的东欧译制片一样夸张生硬。
尽管具备做出一款完整游戏的能力,但这些公司宁愿只提供外包服务,他们无一例外的认为做游戏的风险实在太大。
“做外包的盈利稳定啊,游戏的开发成本太高,万一数据不好,肯定要亏损。”陈然说。在大约两年前,她所在的公司每天都会接到中小CP的订单,有时甚至还要排队。在手游产业繁荣的时期,做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赌博——要么游戏大卖、要么公司关门。在一大批CP死在赌桌上之后,资本的热情明显降温,巨头们开始垄断市场。现在,陈然的公司有80%以上的订单来自大型开发商。
陈然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行业中同行间的互相挖角相当普遍,因此公司愿意开更高的工资留住好员工。除了游戏行业,诸如影视传媒、时尚设计类的公司对人才的需求也愈发旺盛。在2010年之后,这类公司陆续出现在西湖创意谷、LOFT49和白马湖生态创意城这样的创意产业园区里。
目前,杭州共有市级文化创意园区24家,在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米的分布着近5000家文化创意企业和15万从业者,他们在去年为企业贡献了2842.07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在2007年提出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之后,杭州政府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在未来成为娃哈哈和阿里巴巴之后的纳税主力军。
今年一月,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和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去年,杭州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2232.1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GDP增速10.2个百分点,占GDP的22.2%。而以信息服务、设计服务、现代传媒、艺术品等八大行业为重点的核心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19.83亿元,增长36.9%,占比达到91.7%,比上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在杭报集团成功借壳上市后,杭州文创类上市企业达到了 22 家。

四
在2013年10月,杭州在全国率先成立杭州银行文创支行,这家位于黄龙体育中心的支行专门为文创企业提供金融授信,截至目前,有200多家文创企业获得了了超过9亿元的授信支持。
“银行做贷款业务都喜欢有不动产抵押物,但是文创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没有什么抵押担保手段,但有些业务又很烧钱。”这家支行的一位业务负责人说。除提供比其他行业更高一些的风险容忍度,他们为文创企业设计了另一套风险评估体系,比如将知识产权和应收账款作为新的担保方式——比如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权作为抵押物,或是企业与买方签订有效订单后,以销货款为主要还款来源。
王超所在的设计公司曾申请过这项贷款,当时他们为各种各样的商品设计包装——包括藕粉。这家公司所在的丝联166是杭州政府大力推动文创产业时诞生的一个创意产业基地,和北京的798类似,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曾是这大一片包豪斯风格厂房的主人,在上世纪50年代,杭丝联和杭锅、杭氧、杭钢一起见证了杭州工业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
丝联166的正门口有一家叫“蜜桃”的咖啡馆,在大概五年前,这家咖啡馆的隔壁是一家名叫“青桃”的餐厅,但如今这里变成了“老仓库食府”。
“文艺青年体能都不行啊,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来吃饭,就倒闭了。”王超说。每天早上9点50,坐在“老仓库食府”窗口的顾客就能看见背着双肩包的王超来上班。在进办公室之前,王超会用装作若无其事,但实际上非常蹩脚的姿势瞄一眼隔壁公司的前台姑娘——对他来说这就像开始工作的一种仪式,只是没了古时候衙门门口的石狮子,只好用前台来代替。
像王超一样的设计师在丝联166不胜枚举,他们为各种各样的小型公司工作,这些公司的规模都不算大,但创造的利润高的吓人。在某个时期,这些公司都能申请到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财政补贴,这让王超对杭州政府由衷钦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起治理这座城市的交通拥堵,杭州政府更热衷与改善城市的绿化、在湖滨商业街放烟花,或是把遍布大街小巷的垃圾桶都画上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五月初,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落下帷幕,这场动漫节吸引了包括迪斯尼、漫威和东方梦工厂在内的多家国外知名企业。
尽管王超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他每天的工作实际上早已成为了杭州繁荣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缩影。当整条产业链初具雏形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创公司开始迅速的诞生,稳定的发展,开心的数钱,光荣的纳税。

五
有一种观点认为,杭州的富庶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无形土壤。
“有钱嘛,在满足生活必须之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位在当地VC任职的投资总监说,“消费能力提升之后,人们就愿意为好的产品,甚至是内容与知识产权付费,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大部分文创公司卖的都是内容和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大家不再一味追求低价,开始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高品质的服务。这一点在本地的电商和O2O公司表现的很明显,很多公司开始主推高质量的服务与体验,价格也更高。”
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中将杭州描述为“经济大市,资源小市”,“但有着独特的文化优势、丰富的人才优势、优越的环境优势、发达的经济优势和扎实的产业优势”。不可否认的是,繁荣了数百年的杭州旅游业为文化创意提供了数不清的商业机会,在陈然作画的吴山广场,游客们旺盛的购买欲望养活了一大批古玩、服装和工艺品商店,包括陈然画的画和王超设计的包装盒,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慢慢把他们推向了产业链上的一个个细小环节。
相关产业人才的引进也让这里的文创产业快人一步,杭州政府给他们的一系列人才培育政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筑巢引凤”。这使得一些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人才的人——比如自觉混吃等死的王超和爱吃藕粉的陈然——一夜之间成了“紧缺型人才”。在这之前,陈然通过去年发布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顺利拿到了杭州户口。
六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大部分的文化创意公司来说,互联网没有触及到他们业务的核心。几年前,陈然的公司开始用钉钉做内部沟通,用一些SaaS产品进行企业管理,但没有什么互联网工具能代替她手中的画笔和调色板。
“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文化创意产业本质上是个内容产业。内容可以借助互联网去传播、推广,但没办法直接用互联网生产。”上文中的投资总监说,“互联网时代真正发挥整合和垄断作用的是渠道和平台,而不是内容。”至少在大部分互联网产品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创业公司为用户提供工具和渠道,恰恰不生产内容。
他用服装设计行业来举例——在杭州有许许多多淘宝网上的服装大卖家,早先他们购买淘宝网的广告位,甚至是报纸和杂志的广告。如今他们用微信与微博发声,聘用知名的KOL做传播,或是请自媒体写软文。但在这个过程中,服装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尽管渠道与平台意味着话语权,但大部分文创公司并不想盲目扩张。
这位投资总监对一些现象感到担忧,在新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做大渠道、大平台,而不是专心生产内容。“我们很担心这种过度的商业化,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抢渠道、做平台,都想着由自己来整合别人的内容,结果没人做内容了。”他说。这个观点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人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对人类历史影响更大的无疑是后来的谷腾堡印刷术与新教革命。
他看好未来文创产业与VR/AR技术的结合,他觉得这种新的内容载体把创作者的想象空间扩大了数十倍。另一方面,杭州也不缺少这样的创意团队,这位投资总监觉得至少杭州的团队有过硬的能力,不是只会说资本故事。
一些创业公司已经开始了VR内容的探索,位于元谷创意园的二更正在打造国内第一部VR内容视频节目,他们将在迪拜塔、尼加拉瓜大瀑布等世界8个景点取景,采取360全景拍摄的方式,带给观众更震撼的场景体验。
七
袁宏道曾在419年前造访杭州,他从断桥走到苏堤,那些身穿各色丝织品的游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晚游六桥待月记》中,袁宏道说“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在那更早之前,从断桥走到苏堤是杭州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惯就像王超偷瞄的姑娘和陈然吃过的藕粉,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仪式。哪怕在几百年之后,除了平湖秋月和满陇桂雨,这里的人们好像不曾爱过别的东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政府的“大力推进、狠抓落实”和浙江人敏锐的商业嗅觉,浪漫的天性也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赋予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