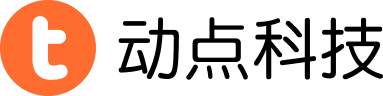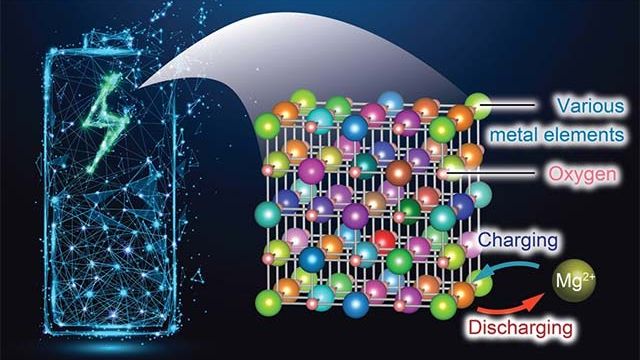本文为动点科技/TechCrunch 中国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当 Facebook 成为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当 Twitter 控制了公众舆论的走向 , 当 Tinder 开始左右我们约会的决定,我们亲手研发用来辅佐我们做出决定的算法正不断凌驾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然而随着我们对算法依赖的与日俱增,从新闻获取到人际交往中都不乏它的身影时,这些行为是我们主动而为之的么?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否逐渐变成了算法流程的倒影?剑桥分析的倾覆会是算法已经入侵我们大脑的预警信号么?
事情本不该如此。在面对铺天盖地的产品、用户以及信息,在面对它们做出选择时,我们发明了一种更好,更快,更便捷的方式来环顾周遭世界。通过既定的参数和一些简单的规则,算法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复杂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数字化战友,能够解决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为我们的选择提供最优解。我家附近最好的餐馆叫什么?谷歌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找苹果地图。特朗普又闹腾出了什么新的幺蛾子?Facebook 会告诉你所有的答案。
假如算法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爱憎喜恶,能够提前知悉我们的所想所得,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么?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必浪费任何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只需去阅读最能佐证我们观点的文章,和与我们最般配的人约会,沉浸在尽在掌握的惊喜之中。想想看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去专注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精心耕耘我们的数字形象,然后再在社交媒体上 po 出这些“身份”。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我们的思想是机器的产物。而埃伦·乌尔曼(Ellen Ullman)也在她的《走近机器》(Close to Machine,暂译)一书中提到过类似的观点。这本书语言了我们在现今生活中的诸多困境。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改善生活所亲手创造的算法已经终结了我们对现实行为的掌控。

我将用以下三个案例阐述算法如何入侵我们的思想,如何操控我们的行为。
从线上购物到线下约会的产品对比
亚马逊的算法使得我们可以浏览和比较商品(或者存下后以备后用),最终促使我们完成购买行为。但这个曾被用来提高我们在线购物体验的工具如今远远超出了其定义的范畴。我们“消化”了这种算法,然后把它运用到了生活中的其它领域,比如人际交往。
如今的约会更像是一种购物行为。它们肇始于社交平台或者社交应用,然后会看到无穷无尽的“选项”,我们对比这些“选项”的匹配特征,我们选出最合乎我们口味的那位备选,完全的契合我们的个人喜好。或者收藏收藏再收藏,因为我们早已对这种梦幻般的选择体验轻车熟路,我们可以自由的游刃于电子购物和线上约会的方寸之中。
网络世界有着无止境的产品供给,如今,人类又加入到了这一行列。“网络敞开了它前所未有的心扉,提供着一切的一切,而你能够从中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而这种选择会带来幸福。多么空虚,梦幻,而又诱惑人心的选择。”乌尔曼在她的另一本《生命代码》中如是写道。
我们都乐于把自己的需求看做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我是如此相信从这些期许中探寻到的诱惑和喜悦会完全的契合我们的渴望。
无论是购物还是约会,我们都被编了程,不断搜寻不断评估不断比较。被算法所驾驭,或者说是被网页的页面设计和代码所驾驭,我们总是在寻找更多的选项。在乌尔曼看来,网络强化了这一念头——“你就是这里的唯一,你的需求就是这里的唯一,算法会帮你找到完美契合你的唯一的唯一。”
简而言之,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方式逐渐变成了我们网络社会生活方式的附庸。算法是一种简化的出路,因为它可以把人类杂乱无章的生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处变成以下两个简单选项:使用明确的算法框架来处理它们,或者仅仅让算法本身为我们做出选择。我们被迫屈服并效力于算法,而非使用技术服务于我们自身。
而这导致了我们所要面对的另一个处境,从最简单的数字化行为开始,为产品和体验打分。
被评分和评论量化了的群体
就像与其它的友善算法一样,量化的算法是为你量身定制,而且只效忠于你的意志。通过你的反馈,归属公司可以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加精准的推送,更多你的历史喜好,这样你就可以继续漫无目的进行消费。
从 Uber 到 Postmate(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顺丰),机会所有与现实生活的互动都被以·-5 星的登记进行划分,被简化成了种种数字评分。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从未如此看重我们的所感所触,从未如此看重我们与他人期待的对比。在突然间,我们可以根据 Airbnb 房主的装帧和布局量化某些主观感受。我们如此急切乃至于令人难以置信——当你神经兮兮的请求五星评论的时候,你的灵魂早已飘出了 Uber 车外,为了提高乘客的评分而手忙脚乱。然后匆忙地浏览留下的反馈。嗯,它总是能以最大的喜悦来满足你。
或许,你该去想一想《黑镜》或者《波特兰迪亚》中的场景,但我们离这种用数字评分取代并且驱使我们生命中所有意义的世界的距离并不算遥远。
我们已经实现了与他人的自动化接触,通过无休止的自我更正不断地量化并且优化这些交互行为。它始于算法,如今却成为生活中的另一个法则。
正如嘉隆·莱尼尔(Jaron Lainier)为《走近机器》所写的简介那样,“我们,用自己的灵感创造了程序,然而却又翻过身来成为它们的养料。随着我们通过这些程序陆续的展开生活,我们接受了被其框选了的现实的事实。”
而这些正是因为技术使得曾经抽象和难以理解的事物得以量化。通过算法,评分和评论变成了信赖,点赞数等同于流行度,而关注粉丝变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算法创造了某种鲍德里亚式的“类像”,评分完全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对照物,并且数字评价显得更加真实,比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更有意义。
面对毫无头绪的现实生活,算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简化的方法,从社会交往和现实社会的不安反馈中摆脱这些尴尬。
然而当我们把编程语言、编程代码或者编程算法当做我们独立思考的组成时,这时的人类天性和人工智能是在合为一体么?我们曾把人工智能当做一种外部力量,某种凌驾于我们之外的产物。假如将要发生的不是机器人占领世界的人工智能危机,而是科技融入到我们的主观意识之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玛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同正在逐渐变成我们感官和肉体延伸的手机一样,算法正在变成我们意识的延伸。一旦他们取代并成为了让我们得以称之为人类的定义的定义时,我们又会怎么办呢?
并且,莱尼尔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疑问:“当计算机更加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语言中时,语言本身是否发生了改变?”

被关键词和流行语自动生成的语言
谷歌会根据关键词对搜寻进行索引。在特定的策略下,SEO(搜索引擎优化)能提高网站的搜索权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通过算法发现什么是影响其结果的原因,然后通过关键词的优化让网站更容易被谷歌抓取。
而我们大脑对信息进行优先级评定的方式和谷歌的算法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关键词,重复回忆以及快速检索来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围绕技术创造的算法最初是用来当做某些问题的解决策略,然而如今却渗透到了我们所作所为的方方面面,从我们为标题的命名到“蹭热点”的推文再到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的自我表达,你看到它的存在了么?
看看这些笼罩在媒体和初创公司上空的流行语。粗略的浏览一下那些顶级初创公司,你会发现吸引人们眼球以及投资人腰包的往往是在名字中加上了“人工智能”、“加密”、“区块链”的公司。
公司的价值正在朝着它们通过关键词向世界所传达出的价值所靠拢。谈判桌上的关键词越流行,吸引到投资者资金的可能性就越大。类似的,一个包含了流行语的标题会更容易被人们点击,所以流行语变得比内文更加重要。所以标题党成为了一种趋势。
这时我们要怎么办?
技术给我们描绘出了清晰的路径,线上购物为丰富的选项提供了简单的应对方式。我们不需要花时间思考,只需按照算法假定的最优解一路点下去,准没错。我们不用对算法的工作方式知根知底,因为它们是隐藏在幕后的,我们无法看到,但算法却可以神奇的把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乌尔曼在《生命代码》中警告的那样:“当我们默许这些复杂的东西退居其后,在幕后掌控我们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去注意到有什么被我们所放弃。当我们和某种并不了解的机制共处共事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成为其零件的风险···当所有的事情都像预期的那样发生时,这种无知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当某些事情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或者糟糕到需要改头换面的时候,除了孤立无援的像造物主一样站在这些产物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想想特朗普时代的假新闻、误导信息以及它们的受众。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如何鼓励批判性思考呢?如何燃起创造的火花?如何让过时的争辩重现光辉?要怎样才能让不同的声音茁壮成长,然后和我们的观点互相激荡?
当我们在由技术所创造的分岔路口惶惶终日,在社交媒体中的一片赞同中生存时,我们要怎样才能看到社会的改变?这里最终所要出现的是,我们会严格的按照算法对我们的设想的那样执行下去。另一种局面是去质疑现状,分析事实然后得出我们的结论。但没有人有时间去这么做。所以我们变成了滚滚 Facebook 的齿轮,轻易就能被各种鼓吹所蛊惑,而我们对此毫不知情,既不知道算法是如何起到效果,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强加进我们思维的过程。
作为算法的奴仆而不是编程人员或者自己的决定的架构师,我们人类的“智能”变成了所谓的“人工”产物。如道格拉斯· 鲁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说的那样,“要么编程,要么被编程。”假如要我们在剑桥分析丑闻和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学到点什么,你要知道,反化社会舆论,影响事件结果,创造一个由数据、接受者以及引理这种虚假意识的机器人构成的世界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而现实更令人无法放心,我们是如此的信任算法,后者则深深根治到了生活框架之中,趋势着绝大多数群体的个人决策,不断地侵入我们的思绪,并且在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愈演愈烈。最终,我们的未来社会会仅在它们的掌控之中。除非我们重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角色,作为编程者而不是被编程者的角色。
编者按 : Adriana Stan 是 W 杂志的公关总监,也是媒体、文化和技术方面的作家。 她也是 Interesting People in Interesting Times 的联合创始人。Mihai Botarel 是 RXM Creative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社会和技术方面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