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东北角的卡塔(Khatta)市场,夜色与火光交织。满载旧电脑和手机的卡车驶入狭窄的街巷,工人们立刻围上去,把废弃的设备一件件卸下。有人点起篝火焚烧电路板,只为从灰烬里扒出几根铜丝;有人用剥线钳逐条拆开电缆,几小时下来,双手满是裂口与灼痕。
千里之外的孟买,一座现代化工厂中,另一番景象正在上演。工人们身穿防护服,在封闭车间操作破碎机和冶炼炉,报废的电脑与电池被粉碎、分选,金、银、钯以及锂、钴等金属被稳定回收,再度流向产业链上游。
这并非摄影师偶然捕捉的孤立画面,而是媒体报道中一再出现的场景。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们并非个例,而是几乎所有印度大城市边缘都在日复一日上演的日常,以及印度电子垃圾产业的双面镜像。
以此为起点,这里的一边是庞大的非正规回收网络,支撑起一个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市场;另一边则是政策与技术推动下正逐渐壮大的正规军,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作为全球第三大电子垃圾制造国,于此,印度正站在产业转型与生态重塑的关键时刻。
从毛细血管到星星之火
正如上文所述,印度电子垃圾回收的版图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在上游,遍布全国的废品收购点和家庭作坊构成了非正规体系的毛细血管;在下游,少数装备精良的企业工厂则代表着仍在成长的正规板块。

2023-24财年,印度产生了约175万公吨电子垃圾,五年内增幅接近73%。其中近六成未被任何形式回收,而进入回收体系的部分,绝大多数(估计高达95%)由非正规从业者完成。据行业调查,这一领域有上百万人依赖谋生:从流动废品商贩卡巴迪瓦拉,到德里锡兰普尔等露天市场的拆解工,再到进行焚烧、电镀的小作坊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灰色网络。
在德里卡塔市场,当地家族势力掌控着八成以上的废料生意。他们通过租赁仓库、雇佣工人、分包环节来构建垄断,被称为“回收业之王”。在这样的体系下,电子垃圾的处理方式往往原始而危险:焚烧电线提取铜,强酸浸泡电路板回收金银,导致工人长期暴露在铅、汞、砷等有害物中。收入也极为微薄——有人每天辛苦拆解10公斤电路板,仅能换来不足50卢比(约合4块钱),而双手满是伤痕。对成千上万的贫困家庭而言,这是难以逃脱的生计陷阱。
相比之下,正规回收体系更像是星星之火——规模虽小,却开始崭露头角。截至2025年,印度在中央污染控制局注册的回收企业有322家,理论处理能力达220万公吨。但现实利用率不足一半,原因在于供应链断裂:分散的家庭和小商户更愿意卖给上门的废品商,而不是联系正规企业。近年来,授权企业处理比例虽从22%提高到43%,仍有过半电子垃圾散落在非正规渠道。
当然,这种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巨大的机遇。电子垃圾中蕴含丰富金属,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甚至高于一吨金矿石。测算显示,印度电子垃圾中潜在可提取的金属价值高达60亿美元,而目前整个产业年产值仅约15.6亿美元。假如能提升正规回收比例,不仅能带来数倍增长空间,还可减少每年约17亿美元的金属进口依赖。由此产生的“城市矿山”的概念,已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兴趣。
但要让这一蓝图落地并非易事,时间仍是这其中必不可缺并且至关重要的构成。同时,伴随着这一进程,这里也将产生新的问题:非正规网络的生命力极强。它们的低成本、灵活性以及对社区的渗透,短期内几乎没有正规企业可以替代。这些占主导地位的非正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将始终是悬在这些矿山上空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废料贸易下的必然
印度电子垃圾回收产业的发展,不仅受国内因素制约,也深深嵌入全球废料贸易与国际政策之中。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将电子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已是公开的秘密,印度正是重要的承接者之一。随着本土消费电子的兴起,印度自身电子废物的规模快速增长,而海外废料也源源不断涌入。尽管官方明令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二手物资”名义下的转移与走私依然屡见不鲜。监管虽在加强,却难以彻底阻断这股灰色潮流。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进口洋垃圾,印度等监管较松的发展中市场正面临更大压力。

与此同时,国际合规趋势也在推动印度回收格局变化。过去十余年,印度的相关法规不断收紧:从2011年的初步管理措施,到2016年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机制,再到2022年的新规,明确要求企业为每公斤废料支付最低补偿,并通过“EPR证书”机制抵消缺口。在政策导向上,印度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提高正规渠道的处理比例,但在执行层面遇到阻力。近年来,三星、LG、日立等跨国厂商已因成本问题起诉印度政府,而这样的事件也远非于此画下句点。
在资本与技术层面,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合作也在增加。瑞士贵金属企业MKS PAMP与印度的Karo Sambhav建立合作项目,计划建设更高效的金属提取设施,以解决本土在高价值部件回收上的技术短板。微软则为Karo Sambhav提供基于Azure的追踪系统,用于提升收集与运输环节的透明度。这些合作本质上回应了政策压力和市场需求,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其能否长期改变产业格局,尚需时间检验。
可以看到,国际力量正通过政策压力与资源输入共同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出口限制与全球环保议程迫使印度提升本土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与资金为本土企业提供了选项。但不难发现,这里的困境也在于,印度能否借此真正推动产业升级,而不是仅仅让国际合作停留在局部示范?这也将是另一个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创业创新:以本土之名
在监管趋严和市场需求扩大的背景下,印度本土自然也在涌现出一批创新企业,试图通过技术和模式推动电子垃圾回收的正规化。
Attero Recycling是典型的技术驱动案例之一。公司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新德里,每年处理超过15万公吨电子废弃物,并额外回收1.5万公吨废旧锂电池。其核心在于自主研发的稀贵金属提炼工艺,可从硬盘、电路板等部件中回收钕、镨、镝,以及金、银、钴、锂等关键资源。随着政府启动国家关键矿产使命,Attero计划两年内将稀土回收产能提升至3万吨,并在海外扩展业务。2025年,其年营收突破1.25亿美元,已成为行业头部企业。
Recyclekaro走的是工厂化路线。公司同样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孟买,运营着一座18英亩的工厂,主要回收企业IT设备和工厂淘汰产品。其年销售额约2500万美元,收入来源包括贵金属和锂、钴、镍等关键材料。政策新规要求厂商为每公斤废弃物支付补偿,使其盈利模式更稳健。作为最早的正规化企业之一,Recyclekaro展示了在专业设施中实现无害化与资源化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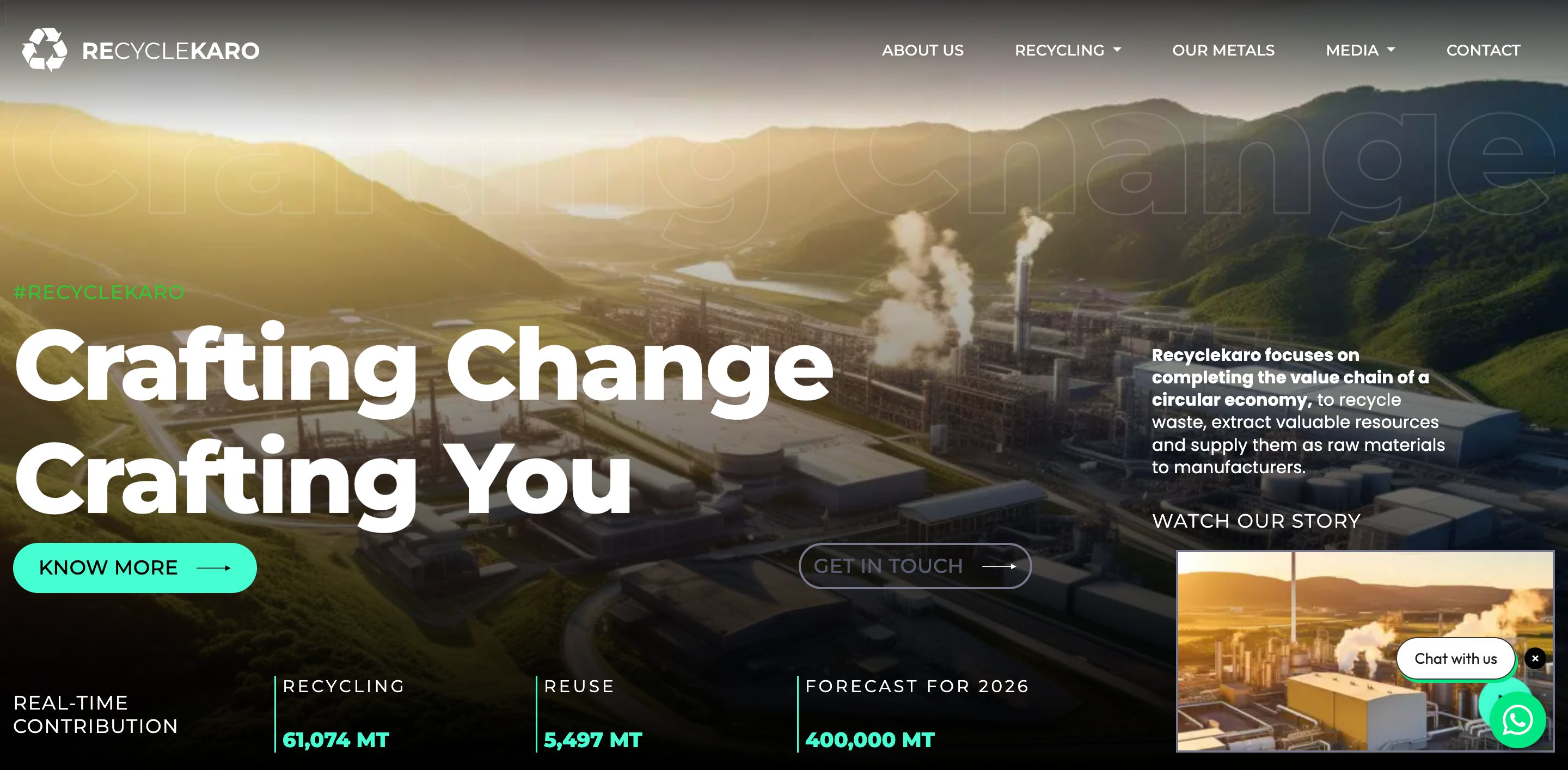
Karo Sambhav则体现了平台化探索。成立于2017年,由前诺基亚高管创办,专注于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服务。它通过数字平台连接制造商、回收企业和非正规回收者,借助App和云端系统建立可追溯网络,确保废料在收集与运输环节不被截留。目前已覆盖70多个城市,吸纳5000多名非正规回收者进入体系。其意义在于证明正规与非正规可以通过技术和激励形成合作关系。
此外,Cashify和Recykal等公司也在快速成长。前者专注于二手手机等数码产品的回收与翻新,累计融资超过2亿美元;后者则搭建B2B废料交易平台,帮助跨国企业完成EPR合规,并获得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投资。这些模式的共同点在于用互联网和资本手段缓解供应链的碎片化,把原本游离在灰色地带的废弃物引入更透明、可控的循环通道。
总体来看,这些企业的实践折射出本土路径的多样化:有的强调技术壁垒,有的依靠工厂规模,有的侧重平台整合。但它们也面临共同难题——如何在保持盈利的同时,真正吸纳大量非正规力量进入规范渠道。这既是市场机遇,也是未来格局的关键。
把未来留在未来
回过头来,印度电子垃圾回收产业正处在裂变与重构的进程中:一边是根深蒂固的非正规帝国,凭借低成本和灵活网络维系着庞大的灰色循环;另一边则是政策、资本和技术催生的新兴力量,试图推动绿色转型与产业升级。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构成了当下印度最真实的产业景象。
当然,这种博弈能否带来质变,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谁能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的探索值得密切注视。无论最终成功与否,这场剧变都将留下一些剧本——不仅为全球电子垃圾治理提供可能的方案,也为快速消费浪潮下的世界敲响警钟:在追逐科技消费高潮的同时,我们是否忘了脚下那座正在膨胀的电子废物巨兽?
印度正在书写的故事,或许正是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寻求循环经济之路的一个缩影。
封面及配图来源:Unsplash及相关企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