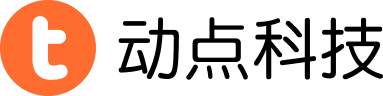在硅谷的创投版图中,很少、甚至从未有过像Andreessen Horowitz(即a16z)这样特立独行的存在。
对传统VC来说,他们会是低调的幕后推手,往往是在不断寻找独角兽,并在获利后功成身退。但a16z颠覆了这一传统。成立于2009年、如今管理着超420亿美元资产的a16z,虽然依然被称作投资机构,但业界对它的定义早已超出了风投的范畴——a16z不再只是一家拥有支票簿的VC,它更像是一家拥有风投业务的媒体公司,并且还在把触手伸向政治领域。
这里,本栏目将试图通过创始人理念、媒体传播、资本扩张、边界突破等维度回顾a16z的变迁。当然,作为这一切的起点(以及本篇所要探讨的内容),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不断漂移的理念也成为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无法绕过的注脚。

价值负四千万美元
在追述a16z的宏大剧本之前,必须先把时间回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
2001年,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寒冬,(曾经的网景创始人)安德森创立的第二家公司Loudcloud陷入绝境。根据当时的财务披露,Loudcloud的市值一度跌至2800万美元,而公司账上实际还躺着约6800万美元的现金。
这显然是一个讽刺拉满的价码。资本市场通过价格信号给出了一个冷酷的判决:这家公司的运营价值为负4000万美元。在当时的华尔街分析师和媒体看来,理性的选择是立刻清算公司,止损离场。他们通过研报和评级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家公司活着的价值低于死去的价值。
然而,安德森做出了违背业界共识的决定。他顶着董事会的巨大压力,裁掉了数百名销售人员,却保留了核心研发团队,强行转型为软件公司Opsware,并最终以16亿美元出售给惠普。
这段在绝境中被市场判死刑的经历,留给a16z的遗产不仅仅是财富,更是一套反脆弱的制度设计。由于不再相信外部评价体系在极端时刻的有效性,a16z在制度上极度推崇“创始人至上”(Founder Friendly)。他们发明了将投票权完全交给创始人的机制,确保企业在逆境中拥有对抗短期市场压力的独断能力。而这种经历,也为a16z后来的激进转向埋下了伏笔。
被软件吞噬的互联网世界
2011年的硅谷正处于移动互联网爆发的前夜。iPhone开始普及,Facebook用户数突破8亿,传统的实体行业开始对数字化感到焦虑,但监管层对科技仍持宽容态度。
那时的马克·安德森,展示出的是一种温和且线性技术进步观。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为什么软件正在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文章,本质上是一份递给主流商业世界的招股说明书。他向华尔街和传统行业解释:软件变革不是破坏,而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它将重塑电影、零售和物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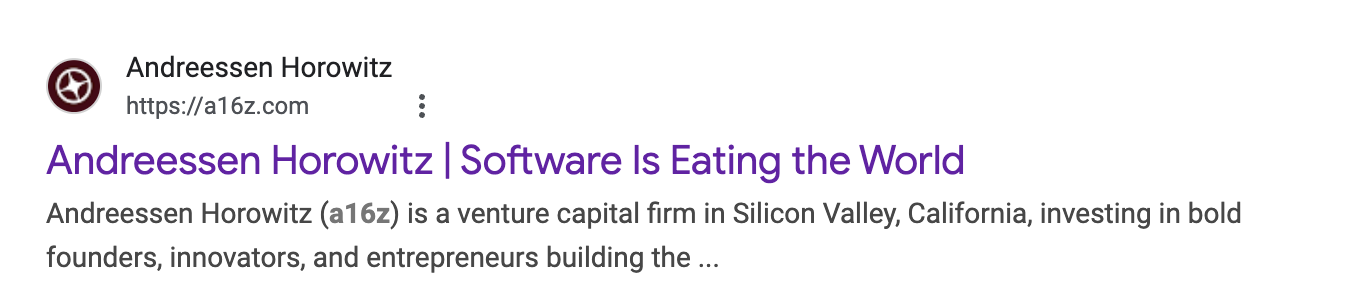
对应到机构策略,这一时期的a16z选择了融入与连接。它扮演着硅谷大使的角色,建立庞大的服务团队,帮助初创公司对接《财富》500强客户。当时的商业媒体乐于将安德森描绘成“极客世界的发言人”,一个连接创新与资本的桥梁。
这种顺势而为的策略也确实带来了惊人的财务回报:a16z在Skype的投资在18个月内获得了3倍回报。而其在Instagram上的一笔25万美元注资,更是风投史上的经典战役。数据显示,当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时,这笔资金膨胀到了7800万美元,实现了惊人的312倍回报。
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比任何公关稿都更有力地证明了“软件吞噬世界”理论的正确性,也让a16z迅速完成了从新锐机构到硅谷顶级权贵的晋升。
拥抱技术、也拥抱规则
十年后,环境发生了剧变。纯软件投资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互联网巨头垄断格局已定。同时,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社会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系统性短板。
在这阶段,至少从文章来看,安德森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位移。在《是时候建设了》(It’s Time to Build)一文中,他的语气从乐观转为严厉。他列举了详细的事实:尽管美国拥有最先进的软件技术,却无法在疫情期间快速生产口罩和呼吸机;旧金山的房价因住房供应短缺而飙升,但新的建设项目却在审批中停滞不前。
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单纯的软件无法吞噬一个被物理法则和行政命令层层包裹的世界。接下来,a16z也开始了赛道迁移,大规模押注“美国活力”(American Dynamism)板块,将数资金注入国防、航天和再工业化等硬科技领域。其中,这一战略最显著的注脚便是a16z对国防科技公司Anduril的重注。
与硅谷传统的轻资产模式截然不同,Anduril制造的是无人机和防御系统,直接挑战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巨头。数据显示,在该战略的推动下,Anduril的估值在短短几年内迅速突破140亿美元,证明了硅谷的逻辑在硬科技领域依然有效。但这同时也意味着a16z必须走出曾经的舒适区。因为在这个新赛道里,搞定规则和搞定技术同样重要。
去定义,而非去适应
如果说投资Anduril还需要在现有的采购体制内寻求合作,那么当时间来到2023年,随着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成为硅谷新风口,硅谷与华盛顿的关系则彻底进入了显性的对立期。
此时的a16z已在加密货币领域押注了超过76亿美元的资金,但这笔巨额资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SEC发起的严厉执法行动,试图从合规层面否定这些资产的价值;而围绕AI爆发的伦理争议,也引发了关于安全审查的激烈讨论。
于此,对这一阶段的a16z来说,成为规则的定义者而不再固守规则的适应者,可能才能带来更多的生存可能。这时,安德森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也随之应运而生。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定的反响。有观点将其描述为一种“反动的未来主义”,批评其试图用技术发展的名义,建立一种不受监督的精英统治。但在硅谷内部,这篇宣言却成为了某种地下圣经。随后,a16z也直接在舆论传播和政治规则两个层面让这一理念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
在舆论战场,a16z不再忍受主流媒体的审视。安德森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大规模拉黑运动,屏蔽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众多批评者。同时,a16z全面执行直接行动(Go Direct)策略,利用自建的播客网络和媒体渠道,绕过记者,构建了一个以自身为载体的舆论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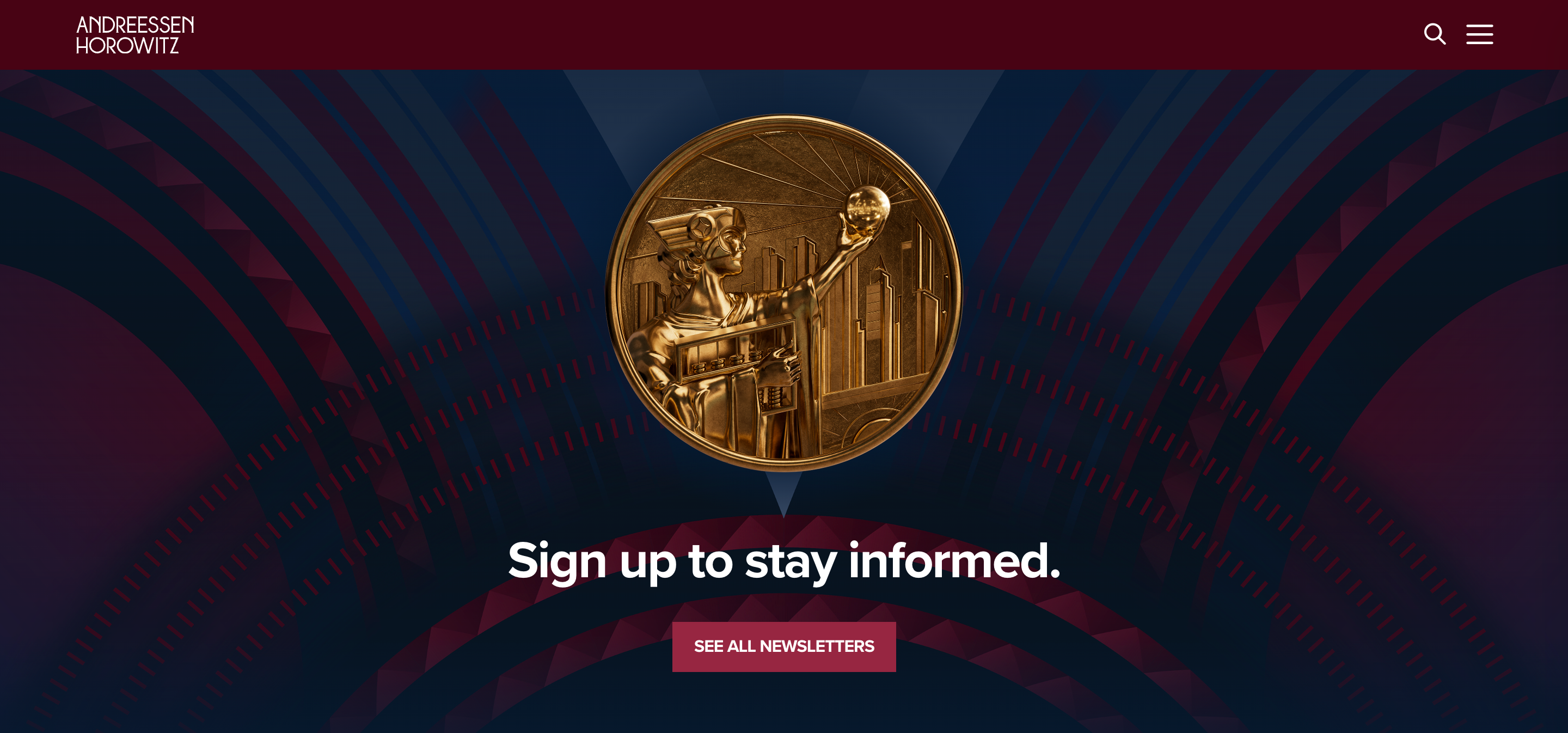
另一层面的案例更加典型。作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Fairshake的核心金主,a16z助推其在2024年周期筹集了超过1.6亿美元的战争基金。这笔巨资不再是用来“交朋友”的,而是被精准用于针对反加密货币的政客——例如向加州众议员Katie Porter发起的数百万美元负面广告攻势,直接展示了资本影响游戏规则的力量。
变化很好,但是不要发生在我家后院
当然,在这些之外,一个微观细节也为安德森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注释。
2022年,当这位呼吁全人类“建设”的投资人,发现自家居住的超级富人区阿瑟顿(Atherton)计划建设几栋多户住宅时,他签署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反对信。他在信中使用了“巨大(IMMENSE)”、“立刻(IMMEDIATELY)”等全大写单词(在西方语境下,基本可以等同于在每句话或者每个字后面都加上了叹号),称这些项目将破坏该地区的生活质量并要求立即移除。
这一事件被媒体无情地嘲讽为“NIMBY(邻避主义)的极致样本”。在一些观点看来,这一举动揭示了硅谷精英阶层最真实、也最复杂的一面:他们希望技术能重塑世界,打破旧有的秩序与束缚,但这种重塑最好不要发生在自家后院。

回顾这一路的历程,从2011年被媒体追捧的“硅谷大使”,到2023年被外界警惕的“规则博弈者”,马克·安德森与a16z的演变,客观上记录了硅谷科技资本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时,为了生存与扩张所做出的适应与应对。
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远非马克·安德森与a16z的全部。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当一家投资机构决定不再遵守旧规则时,这种叛逆又为硅谷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冲击。